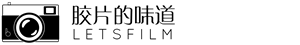еңЁи’ҷи’ҷжө·ж№ҫжіЁи§ҶзқҖжҲ‘зҡ„ V

 еҠ е…ҘеҲ°ж”¶и—ҸеҲ—иЎЁ
еҠ е…ҘеҲ°ж”¶и—ҸеҲ—иЎЁ
дҪңиҖ…пјҡжңүзҗҶеҢ–
жҗ¬еҲ°иҝҷдёӘеІӣдёҠжқҘдҪҸпјҢе·Із»ҸжҳҜдёүе№ҙеүҚзҡ„дәӢжғ…дәҶгҖӮеёҰзқҖдёӨдёӘиЎҢжқҺз®ұгҖҒеҮ еј ж—§з…§зүҮгҖҒдёҖеҸ°иҖҒзӣёжңәпјҢжҗӯзқҖиҲ№пјҢеәҰиҝҮдёҖзүҮи”ҡи“қжө·жҙӢжқҘеҲ°иҝҷйҮҢпјҢдёҖејҖе§ӢиҝҳдёҚд№ жғҜжңүжө·йЈҺеҗ№зқҖзҡ„ж—ҘеӯҗпјҢд№…дәҶе°ұйҖӮеә”дәҶгҖӮжҲ‘дјҡеңЁй»„жҳҸж—¶еёҰзқҖиҖҒзӣёжңәпјҢиө°еҲ°жө·ж№ҫеӨ„жӢҚдёӢеӨӘйҳізҡ„ж ·еӯҗгҖӮ
жҲ‘жЎҢдёҠжңүдёҖеҸ з…§зүҮпјҢеҶ¬еӨ©дёҺжҳҘеӨ©зҡ„еӨ•йҳідёҚеӨӘдёҖж ·гҖӮдҪ жғізңӢеҗ—пјҹжҲ‘еҸҜд»ҘеҜ„з»ҷдҪ гҖӮ
еҜ№дәҶпјҢжҲ‘еҫҲе–ңж¬ўдҪ д№ӢеүҚжҢӮеңЁеўҷдёҠзҡ„йӮЈдәӣз…§зүҮ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жңүйһӢеӯҗзҡ„йӮЈеј пјҢжҲ‘зү№еҲ«е–ңж¬ўйӮЈеј пјҢдҪҶиҮӘд»Һжҗ¬иҝӣжқҘеҗҺпјҢжҲ‘е°ұе°Ҷ他们收иө·жқҘж”ҫиҝӣзҪ®зү©зӣ’йҮҢпјҢеӣ дёәжҲ‘жғіе°Ҷж–°зҡ„жҢӮдёҠеҺ»гҖӮдёҚеҜ№пјҢжҲ‘е·Із»Ҹе°Ҷж–°зҡ„жҢӮдёҠеҺ»дәҶпјҢе®ғ们жҳҜиҖҒз…§зүҮпјҢдёҚиҝҮжқҘеҲ°иҝҷй—ҙжҲҝеӯҗйҮҢеҸҳеҫ—焕然дёҖж–°е‘ўгҖӮ
ж—¶й—ҙдёҚеӨҡдәҶпјҢжҲ‘们жқҘи°Ҳи°Ҳ пј¶ е…Ҳз”ҹеҗ§гҖӮ
еӨ§зәҰжҳҜеңЁеҺ»е№ҙеҶ¬еӯЈгҖӮ
жҲ‘第дёҖж¬ЎеңЁжө·ж№ҫзңӢи§Ғпј¶пјҢжҳҜеңЁеҺ»е№ҙеҚҒдәҢжңҲпјҢеӨ§йӣӘзә·йЈһ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жҲ‘з«ҷеңЁеіЎж№ҫеӨ„пјҢжӢҝиө·зӣёжңәжӯЈиҰҒжӢҚдёӢеӨ•йҳізҡ„ж ·еӯҗпјҢе°ұеңЁйҡ”зқҖдёҖзүҮжө·ж»©зҡ„еҜ№еІёпјҢжңүдёӘж©ҷзәўиүІеӨҙеҸ‘з”·еӯ©еӯҗпјҢеӨҙдёҠжҲҙзқҖй’Ҳз»ҮжҜӣеёҪпјҢз©ҝзқҖжқҫеһ®зҡ„и–„иҚ·иүІи–„иЎ«пјҢзңӢиө·жқҘд№ҹжІЎжңүеҸ‘еҶ·зҡ„ж ·еӯҗпјҢиҝңзңӢжңүдәӣжңҰиғ§зҫҺпјҢе№ҙйҫ„зәҰз•Ҙе’ҢжҲ‘зӣёд»ҝпјҢдёҖзӢ¬иҮӘз«ҷеңЁжө·ж№ҫпјҢжүӢдёҠжҚ§зқҖдёҖдёӘеҸ‘зқҖзәўе…үзҡ„дёңиҘҝпјҢзңҹжҢҡзҡ„еӨ§зңјзҸ зӣҜзқҖжҲ‘иҝҷиҫ№зңӢгҖӮ
жҲ‘зҹҘйҒ“дҪ жғій—®пјҢйӮЈжҳҜи°Ғ家зҡ„еӯ©еӯҗпјҹдҪ еңЁйӮЈеҫ…дёҠдёҖиҫҲеӯҗдәҶжҖҺд»ҺжІЎи§ҒиҝҮпјҹдҪ еҲ«зқҖжҖҘпјҢжҲ‘жғід»–еӨ§жҰӮдёҚжҳҜиҝҷдёҖеёҰзҡ„дәәгҖӮеҪ“дёӢжҲ‘жҖҘзқҖжғізЎ®е®ҡд»–жҳҜдёҚжҳҜзңҹзҡ„жӯЈеҫҖжҲ‘иҝҷиҫ№зңӢпјҢиө¶зҙ§еӣһеҲ°еұӢеӯҗйҮҢжҺҸеҮәжңӣиҝңй•ңпјҢдёҖиҫ№жҡ–зқҖжүӢпјҢеҝ«йҖҹеӣһеҲ°йӮЈдёӘең°ж–№дёҫиө·жңӣиҝңй•ңдёҖзңӢпјҢжҲ‘дҝ©зҡ„зңјзқӣеңЁйҖҸжҳҺзҺ»з’ғзүҮдёҠзӣёдәӨпјҢе°ұеҰӮдё–з•Ңзһ¬й—ҙж–ӯз”өиҲ¬пјҢе•Әеҡ“дёҖеЈ°пјҢзҒ«е…үдёҖзҒӯпјҢд»–еӢҫиө·еҳҙи§’гҖӮ
д»–зҡ„еӨ§зңјзҸ ж•ЈеҸ‘еҮәе№ійқҷзҡ„ж°”жҒҜпјҢжҲ‘дёҖдёӘдәәж…Ңеҫ—еј„жҺүдәҶжңӣиҝңй•ңпјҢд»–жүӢдёҠеҸ‘зқҖзәўе…үзҡ„дёңиҘҝз…§еҫ—д»–зңӢиө·жқҘеҘҪжҡ–гҖӮжҲ‘иҜ•зқҖжғіеӨ§еЈ°й—®йҒ“пјҢд»–жҳҜи°ҒпјҹдҪҸеңЁе“ӘйҮҢпјҹжҳҜи°Ғ家зҡ„еӯ©еӯҗпјҹдҪҶжҲ‘ж”ҫејғдәҶпјҢжҲ‘жІЎжңүжӢҚз…§е°ұеӣһеҲ°еұӢеӯҗйҮҢеҺ»пјҢд»–дёҖдёӘдәәиҝҳз«ҷеңЁйӮЈйҮҢгҖӮ
жҲ‘зҡ„еҝғи·іеҫ—еҸ‘зғ«пјҢжңүеҰӮд»–зЁҚзЁҚжіӣзәўзҡ„еҸҢйўҠгҖӮ
жҲ‘第дәҢж¬ЎзңӢи§Ғд»–пјҢжҳҜеңЁдёҖдёӘзӨјжӢңеҗҺзҡ„й»„жҳҸпјҢжҲ‘д»ҚиҰҒдёҫиө·зӣёжңәжӢҚз…§ж—¶пјҢд»–еҮәзҺ°еңЁз”»йқўдёӯеӨ®пјҢжҲ‘ејәеҝҚеҝғдёӯејәзғҲзҡ„е–ңжӮҰпјҢеҜ№д»–зЁҚеҫ®зӮ№дәҶзӮ№еӨҙпјҢд»–д№ҹзӮ№дәҶзӮ№еӨҙпјҢйқўж— иЎЁжғ…ең°жҠұзҙ§дәҶжүӢдёӯеҸ‘дә®зҡ„дёңиҘҝгҖӮдёҚжҷ“еҫ—иҜҘдёҚиҜҘжҢүдёӢеҝ«й—ЁпјҢиҰҒжҳҜжҢүдәҶд»–дёҚй«ҳе…ҙдәҶжҖҺд№ҲеҠһпјҹ
жҲ‘е·ҰжүӢжӢҝзқҖзӣёжңәпјҢй«ҳдёҫеҸіжүӢжҢҮзқҖпјҢиҜ•зқҖй—®д»–иғҪдёҚиғҪеё®д»–жӢҚеј з…§пјҢд»–зңӢи§ҒдәҶпјҢиҪ»иҪ»ең°ж‘Үж‘ҮеӨҙпјҢиЎЁзӨәдёҚиЎҢгҖӮжҲ‘д№ҹеҲҶдёҚжё…жҘҡпјҢжҳҜдёҚиЎҢпјҢдёҚз”ЁпјҢдёҚиҰҒпјҢиҝҳжҳҜдёҚиғҪгҖӮ
жҲ‘еҸҲжҢҮдәҶжҢҮд»–жүӢдёӯйӮЈдёӘеҸ‘зәўзҡ„дёңиҘҝпјҢиҜ•зқҖй—®д»–йӮЈжҳҜд»Җд№ҲпјҢд»–дҪҺеӨҙзңӢдәҶзңӢйӮЈдёңиҘҝпјҢ然еҗҺжҠ¬еӨҙзңӢжҲ‘пјҢжҲ‘жӢҝиө·жңӣиҝңй•ңпјҢд»–еғҸжҳҜиҰҒиҜҙд»Җд№Ҳдјјзҡ„еҚҙеҸҲйҳ–дёҠдәҶеҳҙе·ҙгҖӮ
иҖҒе®һиҜҙпјҢеңЁжҲ‘жқҘеҲ°иҝҷдёӘең°ж–№д№ӢеүҚпјҢжҲ‘е°ұеҒҡеҘҪеҝғзҗҶеҮҶеӨҮпјҢзҹҘйҒ“дҪ дјҡжҳҜе…ҲзҰ»ејҖзҡ„гҖӮжҲ‘дёҖзӣҙйғҪж— жі•д№ жғҜеҪ•йҹіеёҰйҮҢиҮӘе·ұзҡ„еЈ°йҹіпјҢйӮЈеҗ¬иө·жқҘеғҸжңәеҷЁдәәдёҖж ·еҲ«жүӯпјҢеёҢжңӣдҪ еҗ¬иө·жқҘжҲ‘зҡ„еЈ°йҹідёҚдјҡеӨӘжҖӘпјҢиҮіе°‘еңЁйҒ“еҲ«ж—¶жҲ‘зҡ„е—“еӯҗеҸҲжҳҫеҫ—жӣҙдҪҺжІүдёҖдәӣдәҶгҖӮ
иҮӘд»Һ第дёҖж¬ЎйҒҮи§Ғд»–д№ӢеҗҺпјҢжҲ‘дёҖзӣҙйғҪжҖқеҝөзқҖд»–пјҢжңүеҰӮеҶ¬еӯЈзҡ„еӨ•йҳіиҲ¬д»ӨдәәзүөжҢӮгҖӮдҪ д№ҹеҲ«еӨӘеңЁж„Ҹиҝҷ件дәӢпјҢдҪ д№ҹи®ёиҝҳеҝҷзқҖе°Ҷж–°жңӢеҸӢзҡ„з…§зүҮжҢӮдёҠеўҷе‘ўгҖӮ
еҪ“жҲ‘第дёүж¬Ўи§ҒеҲ°д»–ж—¶пјҢд»–зҡ„е·ҰжүӢжҚ§зқҖйӮЈдёӘеҸ‘зәўзҡ„дёңиҘҝпјҢеҸіжүӢжӢҝзқҖдёҖж”Ҝй»‘иүІжңӣиҝңй•ңгҖӮд»–дёҫиө·жңӣиҝңй•ңпјҢеҜ№еҮҶжҲ‘жүҫеӣһзҒөйӯӮзҡ„еҸҢзңјгҖҒиғҖзәўзҡ„и„ёйўҠгҖҒиө·дјҸдёҚе®ҡзҡ„иғёеҸЈпјҢе’»дёҖеЈ°еҸ‘е°„пјҢе°„дёӯдәҶжҲ‘йЎҪејәдё”и„Ҷејұзҡ„еҝғи„ҸгҖӮ
жҲ‘жү¶зқҖиғёеҸЈгҖҢе•ҠгҖҚдёҖеЈ°ең°еҖ’дёӢпјҢд»–ж”ҫдёӢжңӣиҝңй•ңпјҢеҳҙеҪўеғҸжҳҜиҜҙдәҶдёҖеЈ° вҖңVictory."
йӮЈе°ұеҘҪжҜ”е”ұиө·дәҶдёҖйҰ–жјӮдә®зҡ„жӯҢгҖӮ
VictoryпјҢиғңеҲ©гҖӮе°ұеңЁйӮЈж—¶зҡ„жӯӨеҲ»пјҢиў«йҖҸиҝҮжңӣиҝңй•ңзүҮе°„жқҖзҡ„жҲ‘пјҢпј¶ жҲҗеҠҹиөўеҫ—жҲ‘зҡ„еҝғгҖӮ
дҪ еҸҜеҲ«йҡҫиҝҮеӣ жӯӨе°ұжҠҠеҪ•йҹіеёҰе…ідәҶгҖӮ
еҪ“жҲ‘и§ҒеҲ°пј¶ е…Ҳз”ҹ第дәҢеҚҒдёҖж¬Ўж—¶пјҢе·Із»ҸжҳҜжҳҘжҡ–иҠұејҖзҡ„еӯЈиҠӮпјҢд»–еғҸжҳҜеңЁзӯүзқҖжҲ‘еҮәзҺ°иҲ¬пјҢи„ёдёҠйңІеҮәе№іж—¶жІЎи§ҒиҝҮзҡ„з„ҰиәҒпјҢзӣҙеҲ°жҲ‘еҮәзҺ°еңЁд»–зңјеүҚпјҢд»–жүҚе®ҡдёӢдәҶзңјзҘһпјҢеҜ№зқҖжҲ‘зӮ№зӮ№еӨҙгҖӮ
жҲ‘зӮ№зӮ№еӨҙпјҢд»–зӘҒ然ж”ҫејҖеҸҢжүӢпјҢеҸ‘зқҖзәўе…үзҡ„дёңиҘҝжү‘йҖҡдёҖеЈ°жҺүе…Ҙжө·йҮҢпјҢеңЁжө·йқўдёҠж•ЈејҖпјҢеҪўжҲҗдёҖйҒ“зәўиүІжҡ–жөҒпјҢжөҒеҲ°жө·е№ізәҝдёӯеӨ®пјҢжҲҗдәҶдёҖдёӘе·ЁеӨ§зҡ„еӨ•йҳігҖӮ
жҲ‘зңӢеҫ—еҸ‘жҘһпјҢжүӢдёӯзҡ„зӣёжңәиҗҪеңЁең°дёҠпјҢеӣһиҝҮзҘһжқҘж—¶пјҢпј¶ ж¶ҲеӨұдәҶгҖӮ
дҪ еӨ§жҰӮжғій—®д»–еҺ»е“ӘйҮҢдәҶеҗ§пјҢжҲ‘е‘ҠиҜүдҪ пјҢпј¶ е°ұжҳҜеӨ•йҳіе•ҠпјҢд»–е°ұжҳҜйӮЈжҜҸдёӘй»„жҳҸдјҡеңЁжө·е№ійқўзј“зј“иҗҪдёӢзҡ„еӨ•йҳіпјҢе°ұжҳҜжҲ‘еҫҖж—Ҙдёҫиө·зӣёжңәжӢҚдёӢзҡ„йӮЈдёӘж©ҷзәўиүІзҡ„еӨ•йҳігҖӮзӯүжҲ‘еӣһеҲ°жҲҝеӯҗйҮҢпјҢжҲ‘
жүҚзӢ¬иҮӘжңӣзқҖзӘ—еӨ–иҝҹиҝҹдёҚиҗҪдёӢзҡ„еӨ•йҳіе“ӯдәҶиө·жқҘпјҢдёҖиҫ№жӢӯзқҖж»ҡзғ«зҡ„жіӘдёҖиҫ№дёҫиө·зӣёжңәжӢҚдёӢдәҶд»–зҡ„ж ·еӯҗгҖӮиҝҷж—¶еӨ•йҳіжүҚеғҸжңүдәәжӢүзқҖеҚ·еҠЁеёғеёҳиҲ¬зј“зј“иҗҪдёӢгҖӮ
дёҖеҲҮйғҪиҗҪ幕дәҶпјҢдҪ иҜҙжҳҜдёҚжҳҜпјҢеңЁ пј¶ зҰ»ејҖд№ӢеҗҺпјҢжҳҜдёҚжҳҜжҲ‘дәӨд»ҳеҮәеҺ»зҡ„зҲұйғҪеҘүзҢ®з»ҷеӨ§жө·дәҶгҖӮ
ж—ҘеӯҗеҸҲеӣһеӨҚжӯЈеёёпјҢжҲ‘дёҖеҰӮеҫҖеёёең°еңЁй»„жҳҸж—¶иө°еҲ°жө·ж№ҫжӢҚдёӢжҜҸеӨ©зҡ„еӨ•йҳіпјҢжҲ‘жҖ»жҳҜжңҹеҫ…иғҪеңЁеҜ№йқўзҡ„жө·ж№ҫи§ҒеҲ°д»–пјҢжүҖд»ҘйўҲеӯҗдёҠжҖ»дјҡиғҢзқҖдёҖеҸ°жңӣиҝңй•ңпјҢжҜҸжңӣдёҖж¬ЎпјҢжңҹзӣјзҡ„еҝғе°ұи¶ҠжҳҜжІүйҮҚпјҢжҲ‘жҜҸжҜҸеңЁжўҰйҮҢи§ҒеҲ°д»–пјҢд»–д»ҚжҳҜйӮЈж ·йҒҘиҝңдё”жёәе°ҸпјҢж°ёж°ёиҝңиҝңйғҪж— жі•еҗ¬и§Ғд»–иҜҙиҜқзҡ„еЈ°йҹігҖӮ
жҲ‘жҖқеҝөд»–пјҢзӣҙеҲ°еҶ¬еӯЈгҖӮ
еҚҒдәҢжңҲдёүеҚҒж—ҘпјҢзүҮзүҮйӣӘиҠұиҗҪеңЁжҲ‘иӮ©дёҠж—¶пјҢжҲ‘е·Із»Ҹе°ҶеҺ»е№ҙзҡ„з…§зүҮе…ЁжӢҝдёӢжқҘпјҢ收еңЁзӣ’еӯҗйҮҢпјҢеўҷдёҠдёҚеҶҚжҢӮж»ЎзӣёзүҮпјҢеұӢеӯҗйҮҢжҳҫеҫ—жӣҙеҠ з©әиҚЎпјҢзҠ№еҰӮд»ҺжңӘжңүдәәз”ҹжҙ»иҝҮгҖӮдҪ д№ҹи®ёжғій—®дёәд»Җд№ҲжҲ‘иҝҷд№ҲеҒҡпјҢдёҚиҝҮжҲ‘ж— жі•еӣһзӯ”дҪ пјҢжҲ‘иҝҷд№ҲеҒҡ并没жңүд»Җд№ҲеҺҹеӣ гҖӮ
жҲ‘дёҖдёӘдәәз«ҷеңЁжө·ж№ҫпјҢжІЎжңүеёҰдёҠжңӣиҝңй•ңпјҢд№ҹжІЎеёҰдёҠзӣёжңәпјҢеӣҙзқҖеӣҙе·ҫз«ҷеңЁеұӢеӯҗеүҚпјҢеҶ¬еӨ©е°ұеҰӮд»ҘеҫҖдёҖж ·еҶ·пјҢж°”еҖҷдёҠжІЎжңүеӨӘеӨ§зҡ„еҸҳеҢ–пјҢеӣӣеӯЈж°ёиҝңеҫҲжҳҜеҲҶжҳҺпјҢжҲ‘еҘҪйҡҫжғіеғҸжҲ‘зҡ„зҲұе°ұиҝҷж ·еҒңжӯўдәҶпјҢеҰӮж•…йҡңзҡ„ж—ӢиҪ¬жңЁй©¬иҲ¬зҡ„еҒңжӯўдәҶгҖӮеҫҲжҠұжӯүпјҢжҲ‘жЎҢдёҠиҝҳз•ҷзқҖжҲ‘иў«д»–еҮ»з ҙзҡ„жңӣиҝңй•ңй•ңзүҮпјҢеҫҲжҠұжӯүжҲ‘зҲұеҫ—з»қжңӣдё”иҝҹй’қгҖӮ
йӮЈеӨ©еҲ°дәҶй»„жҳҸж—¶пјҢзӘҒ然жңүдәәз«ҷеңЁжҲ‘иә«еҗҺпјҢдҪҶжҲ‘жІЎжңүеӣһиҝҮеӨҙзңӢпјҢжҲ‘зҹҘйҒ“йӮЈжҳҜи°ҒгҖӮеҪ“д»–еңЁжҲ‘и·қзҰ»дёҚеҲ°еҚҒе…¬еҲҶзҡ„иә«еҗҺеҶҚж¬Ўдёҫиө·жңӣиҝңй•ңеҜ№еҮҶжҲ‘еӨұеҺ»зҒөйӯӮзҡ„еҸҢзңјгҖҒиӢҚзҷҪзҡ„и„ёйўҠгҖҒеҒңжӯўи·іеҠЁзҡ„иғёеҸЈпјҢе’»дёҖеЈ°еҸ‘е°„пјҢе°„з©ҝдәҶжҲ‘жҒ’д№…д»ҘжқҘиғҖж»Ўж— йҷҗжҖқеҝөзҡ„иәҜдҪ“гҖӮжҲ‘зҹҘйҒ“йӮЈжҳҜи°ҒгҖӮ
жҲ‘дҝ©еҗҢж—¶еә”еЈ°еҖ’дёӢпјҢд»–з”Ёе°Ҫе…ЁеҠӣжҠұзҙ§жҲ‘пјҢеңЁжҲ‘иҖіиҫ№е‘өж°”пјҢдҪ“жё©зғ«еҫ—иһҚеҢ–дәҶйӣӘпјҢж©ҳзәўиүІиЎҖжөҶд»ҺжҲ‘дҝ©зҡ„иғёеҸЈжәўеҮәпјҢеҪўжҲҗдёҖйҒ“зәўжөҒпјҢеӨ•йҳіиҘҝдёӢпјҢжӯӨеӨ„з•ҷдёӢдёҖеј иҖҒз…§зүҮпјҢз…§зүҮдёҠжңүд»–жңүжҲ‘зҡ„зҺ»з’ғзўҺзүҮгҖӮ
з °дёҖеЈ°пјҢз °з °дёӨеЈ°пјҢVictoryгҖӮ
зҢ®з»ҷ V
Flipermag иҪ¬иҪҪжҺҲжқғпјҢиҪ¬иҪҪиҜ·жіЁжҳҺеҮәеӨ„гҖ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