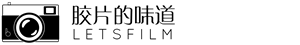第еӣӣз« пјҡж·ұеӨңзҡ„зӢ¬йЈҹиҖ…

 еҠ е…ҘеҲ°ж”¶и—ҸеҲ—иЎЁ
еҠ е…ҘеҲ°ж”¶и—ҸеҲ—иЎЁ
еӯӨзӢ¬дёҚжҳҜжІЎжңүдәәйҷӘдҪ еҗғйҘӯпјҢиҖҢжҳҜдҪ еҗғйҘӯ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зӯ·еӯҗеҸӘйңҖиҰҒеӨ№дёҖдёӘдәәзҡ„д»ҪйҮҸгҖӮйӮЈз§ҚеӨҡдҪҷзҡ„зІҫзЎ®пјҢжүҚжҳҜжңҖж®ӢеҝҚзҡ„гҖӮдҪ дјҡеҸ‘зҺ°иҮӘе·ұдёӢж„ҸиҜҶең°е°‘д№°дәҶдёҖд»ҪпјҢе°‘зғӯдәҶдёҖд»ҪпјҢе°‘еқҗдәҶдёҖдёӘдҪҚзҪ®гҖӮиҝҷдәӣж— ж•°дёӘеҫ®е°Ҹзҡ„вҖңе°‘вҖқзҙҜз§Ҝиө·жқҘпјҢе°ұжһ„жҲҗдәҶеӯӨзӢ¬зҡ„зү©зҗҶдҪ“з§Ҝ вҖ”вҖ” е®ғдёҚжҳҜз©әзҡ„пјҢе®ғжҳҜдёҖеқ—е®һеҝғзҡ„гҖҒиў«вҖңзјәеёӯвҖқеЎ«ж»Ўзҡ„й“…еқ—гҖӮ
еҮҢжҷЁдёҖзӮ№зҡ„дҫҝеҲ©еә—пјҢзҒҜе…үжғЁзҷҪпјҢеғҸеӨӘе№ій—ҙзҡ„з…§жҳҺгҖӮ
е®ғдёҚеғҸжҡ—жҲҝйҮҢзҡ„зәўзҒҜйӮЈж ·д»Ғж…ҲпјҢиғҪе®№зәіжҡ§жҳ§зҡ„йҳҙеҪұгҖӮиҝҷйҮҢзҡ„жҜҸдёҖеҜёз©әй—ҙйғҪиў«й«ҳжөҒжҳҺзҡ„ж—Ҙе…үзҒҜз®ЎејәиЎҢз…§дә®вҖ”вҖ”еҲәзңјпјҢж— жғ…пјҢеғҸдёҖеј иҝҮеәҰжӣқе…үзҡ„еә•зүҮпјҢжүҖжңүзҡ„еұӮж¬ЎйғҪиў«жјӮзҷҪпјҢиҝһиәІи—Ҹзҡ„йҳҙеҪұйғҪиў«жқҖжӯ»дәҶгҖӮ
жҺЁй—ЁиҝӣеҺ»зҡ„зһ¬й—ҙпјҢеҶ·зғӯжё©е·®и®©жҲ‘зҡ„зңјй•ңзһ¬й—ҙиө·дәҶдёҖеұӮзҷҪйӣҫгҖӮ
дё–з•ҢеңЁиҝҷдёҖз§’й’ҹеҶ…еӨұз„ҰдәҶгҖӮеҸҜиғҪжҳҜеӣ дёәеңЁеӨ–йқўеғҸдёӘзҢҺдәәдёҖж ·жёёиҚЎдәҶдёҖж•ҙеӨ©пјҢйҖҸж”ҜдәҶеӨӘеӨҡзҡ„вҖңи§ӮзңӢвҖқпјҢжӯӨеҲ»зҹӯжҡӮзҡ„еӨұжҳҺеҸҚиҖҢжҳҜдёҖз§Қдј‘жҒҜгҖӮ
жҲ‘ж‘ҳдёӢзңјй•ңпјҢиғЎд№ұж“ҰдәҶж“ҰпјҢдё–з•ҢеҶҚж¬Ўй”җеҲ©еҫ—еҲәзңјгҖӮ
д№°дәҶдёҖдёӘдёүи§’йҘӯеӣўгҖӮ收银е‘ҳй—®иҰҒдёҚиҰҒеҠ зғӯпјҢжҲ‘ж‘ҮдәҶж‘ҮеӨҙгҖӮ
еқҗеңЁзӘ—иҫ№зҡ„еҗ§еҸ°дҪҚпјҢжҲ‘жңәжў°ең°еҫҖеҳҙйҮҢеЎһзқҖеҶ·жҺүзҡ„зұійҘӯгҖӮжө·иӢ”е·Із»ҸиҪҜдәҶпјҢеғҸж№ҝе“’е“’зҡ„зәёиҙҙеңЁиҲҢеӨҙдёҠгҖӮ
ж—Ғиҫ№еқҗзқҖдёүдёӘеҲҡдёӢеӨңзҸӯзҡ„е№ҙиҪ»дәәпјҢеӨ§жҰӮжҳҜйҷ„иҝ‘зҗҶеҸ‘еә—зҡ„еӯҰеҫ’пјҢйЎ¶зқҖдёүйў—йўңиүІеҗ„ејӮзҡ„еӨҙгҖӮ他们еӨ§еЈ°з¬‘зқҖпјҢдә’зӣёжҺЁжҗЎпјҢжүӢжңәйҮҢж’ӯж”ҫзқҖжҹҗдёӘзҹӯи§Ҷйў‘зҡ„зҪҗеӨҙ笑声гҖӮ
е·ЁеӨ§зҡ„笑声еңЁзӢӯзӘ„зҡ„дҫҝеҲ©еә—йҮҢеӣһиҚЎпјҢеғҸеҠЈиҙЁйҹіз®ұеҸ‘еҮәзҡ„зҲҶз ҙйҹіпјҢж’һеҮ»зқҖжҲ‘зҡ„иҖіиҶңгҖӮжҲ‘ж„ҹеҲ°дёҖйҳөз”ҹзҗҶжҖ§зҡ„еҸҚиғғгҖӮиҝҷдёҚжҳҜжё…й«ҳпјҢиҝҷжҳҜй•ҝжңҹзҡ„зӢ¬еұ…з”ҹжҙ»еёҰжқҘзҡ„жҺ’ејӮеҸҚеә”гҖӮеғҸдёҖдёӘж·ұжҪңзҡ„дәәзӘҒ然被жӢүеҮәж°ҙйқўпјҢиӮәйғЁж— жі•йҖӮеә”иҝҷз§Қй«ҳжө“еәҰзҡ„зӨҫдәӨж°§ж°”гҖӮжҲ‘жғіеҜ№д»–们еӨ§е–ҠвҖңй—ӯеҳҙвҖқпјҢдҪҶжңҖеҗҺпјҢжҲ‘еҸӘжҳҜеҫҖи§’иҗҪйҮҢзј©дәҶзј©пјҢжҠҠеӨҙеҹӢеҫ—жӣҙдҪҺгҖӮ
зҺ»з’ғзӘ—еӨ–пјҢдёҖеҸӘж©ҳзҷҪзӣёй—ҙзҡ„жөҒжөӘзҢ«жӯЈеңЁзҝ»еһғеңҫжЎ¶гҖӮе®ғеҠЁдҪңзҶҹз»ғпјҢд»ҺдёҖдёӘз ҙдәҶзҡ„иўӢеӯҗйҮҢеҸјеҮәдёҖж №еҗғеү©зҡ„зғӨиӮ гҖӮе®ғжІЎжңүжҖҘзқҖеҗғпјҢиҖҢжҳҜиӯҰжғ•ең°жҠ¬еӨҙзңӢдәҶдёҖеңҲеӣӣе‘ЁгҖӮ
йӮЈзңјзҘһжҲ‘зҶҹжӮүгҖӮ
жҲ‘们жҳҜеҗҢиЎҢгҖӮе®ғеңЁеһғеңҫжЎ¶йҮҢзҝ»жүҫйЈҹзү©пјҢжҲ‘еңЁеҹҺеёӮзҡ„еәҹеўҹйҮҢзҝ»жүҫи®°еҝҶгҖӮжҲ‘们йғҪжҳҜйқ зқҖеҲ«дәәзҡ„ж®Ӣзҫ№еҶ·зӮҷжҙ»зқҖзҡ„з”ҹзү©пјҢеңЁиҝҷдёӘе·ЁеӨ§зҡ„еҹҺеёӮиғғеӣҠйҮҢпјҢиҜ•еӣҫдёҚиў«ж¶ҲеҢ–жҺүгҖӮ
е…ідёңз…®зҡ„зғӯж°”д»ҺжҹңеҸ°йҮҢйЈҳеҮәжқҘпјҢеёҰзқҖй…ұжІ№гҖҒе‘ізІҫе’ҢзҷҪиҗқеҚңз…®д№…дәҶзү№жңүзҡ„зғӮзҶҹз”ңе‘ігҖӮиҝҷиӮЎе‘ійҒ“еғҸдёҖйў—й’үеӯҗпјҢзӣҙжҺҘеҮҝиҝӣдәҶжҲ‘зҡ„и„‘дёӯгҖӮ
йӮЈз§Қе‘ійҒ“и®©жҲ‘жғіиө·д»Җд№Ҳ вҖ”вҖ”
жҳҜеҘ№гҖӮ
еҘ№е–ңж¬ўдҫҝеҲ©еә—зҡ„е…ідёңз…®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зҷҪиҗқеҚңгҖӮжҜҸж¬Ўи·ҜиҝҮдҫҝеҲ©еә—еҘ№йғҪдјҡд№°дёҖд»ҪпјҢ然еҗҺжҠҠеҗёж»ЎжұӨжұҒзҡ„иҗқеҚңеқ—жҲіеңЁз«№зӯҫдёҠпјҢдёҫеҲ°жҲ‘еҳҙиҫ№пјҢйқһиҰҒжҲ‘еҗғгҖӮ
вҖңжҲ‘дёҚе–ңж¬ўеҗғиҗқеҚңпјҢжңүжҖӘе‘ігҖӮвҖқжҲ‘жҖ»жҳҜиәІгҖӮ
вҖңеҗғеҳӣгҖӮиҝҷжҳҜеҘҪдёңиҘҝпјҢеҶ¬еҗғиҗқеҚңеӨҸеҗғе§ңгҖӮвҖқеҘ№з¬‘еҳ»еҳ»ең°еҫҖжҲ‘еҳҙйҮҢеЎһпјҢвҖңдҪ дёҚе–ңж¬ўиҗқеҚңпјҢдҪҶдҪ еҫ—е–ңж¬ўжҲ‘е–ӮдҪ гҖӮвҖқ
йӮЈеҸҘиҜқйҮҢзҡ„йҖ»иҫ‘пјҢеҗ¬иө·жқҘеғҸдёҖдёӘж— и§Јзҡ„и°ңиҜӯгҖӮ
жҲ‘究з«ҹжҳҜи®ЁеҺҢиҗқеҚңзҡ„е‘ійҒ“пјҢиҝҳжҳҜдҫқжҒӢйӮЈдёӘжҠҠиҗқеҚңйҖ’еҲ°жҲ‘еҳҙиҫ№зҡ„жүӢеҠҝпјҹеҰӮжһңйӮЈдёӘе–ӮжҲ‘зҡ„дәәдёҚеңЁдәҶпјҢиҝҷеқ—иҗқеҚңе°ұеҸӘжҳҜдёҖеқ—жҷ®йҖҡзҡ„гҖҒз…®зғӮдәҶзҡ„жӨҚзү©ж №иҢҺгҖӮ
жҲ‘зӣҜзқҖе…ідёңз…®зҡ„и’ёжұҪпјҢиҜ•еӣҫи®°иө·еҘ№иҜҙиҝҷеҸҘиҜқж—¶зҡ„иЎЁжғ…гҖӮ
и®°дёҚжё…дәҶгҖӮ
жҲ‘еҸӘи®°еҫ—йӮЈеҸҘиҜқзҡ„ж–Үеӯ—пјҢеғҸеӯ—幕дёҖж ·жө®зҺ°еңЁи„‘жө·йҮҢпјҢдҪҶдёҚи®°еҫ—еҘ№иҜҙиҜқж—¶зҡ„еЈ°и°ғпјҢдёҚи®°еҫ—еҘ№еҳҙи§’зҡ„еј§еәҰгҖӮе°ұеғҸйӮЈеј еӨұз„Ұзҡ„з…§зүҮдёҖж · вҖ”вҖ” еҸӘжңүиҪ®е»“пјҢжІЎжңүеҶ…е®№гҖӮ
д»ҠеӨ©жӢҚзҡ„йӮЈдәӣз…§зүҮеғҸе№»зҒҜзүҮдёҖж ·еңЁжҲ‘и„‘еӯҗйҮҢй—ӘиҝҮгҖӮ
дёҖеҜ№жғ…дҫЈеңЁдҫҝеҲ©еә—й—ЁеҸЈеҲҶдёҖжқҜзғӯйҘ®пјҢеҘіз”ҹжҠҠеҗёз®ЎйҖ’з»ҷз”·з”ҹпјҢз”·з”ҹе–қдәҶдёҖеҸЈеҸҲйҖ’еӣһеҺ» вҖ”вҖ” йӮЈдёӘеҠЁдҪңйҮҢжңүдёҖз§ҚдёҚйңҖиҰҒиҜӯиЁҖзҡ„й»ҳеҘ‘гҖӮ
еҸҰдёҖеҜ№жғ…дҫЈе№¶жҺ’еқҗеңЁзӘ—иҫ№еҗғдҫҝеҪ“пјҢеҘіз”ҹжҠҠиҮӘе·ұдёҚзҲұеҗғзҡ„蔬иҸңеӨ№еҲ°з”·з”ҹзў—йҮҢ вҖ”вҖ” йӮЈжҳҜдёҖз§ҚеҸӘжңүй•ҝжңҹзӣёеӨ„жүҚдјҡжңүзҡ„иҮӘ然гҖӮ
жҲ‘е’ҢеҘ№д№ҹиҝҷж ·еҒҡиҝҮеҗ—пјҹ
жҲ‘еҠӘеҠӣеӣһжғігҖӮеҘҪеғҸжңүгҖӮеңЁе“ӘйҮҢпјҹжҳҜе№ҝе·һиҝҳжҳҜйҰҷжёҜпјҹжҳҜжқӯе·һиҝҳжҳҜеҺҰй—ЁпјҹжҲ‘и®°еҫ—жҳҜдёҖжқҜеҘ¶иҢ¶пјҢдҪҶжҲ‘дёҚзЎ®е®ҡйӮЈжҳҜзңҹе®һзҡ„и®°еҝҶпјҢиҝҳжҳҜжҲ‘ж №жҚ®д»ҠеӨ©зңӢеҲ°зҡ„з”»йқў"еҲ¶йҖ "еҮәжқҘзҡ„дјӘиҜҒгҖӮ
иҝҷе°ұжҳҜй—®йўҳжүҖеңЁгҖӮ
жҲ‘жӢҚеҫ—и¶ҠеӨҡпјҢи¶ҠеҲҶдёҚжё…е“ӘдәӣжҳҜиҮӘе·ұзҡ„и®°еҝҶпјҢе“ӘдәӣжҳҜеҲ«дәәзҡ„з”»йқўеңЁжҲ‘и„‘еӯҗйҮҢз•ҷдёӢзҡ„ж®ӢеҪұгҖӮ
и®°еҝҶиў«жұЎжҹ“дәҶгҖӮ е°ұеғҸжҳҫеҪұж¶Іиў«еҸҚеӨҚдҪҝз”ЁпјҢжҜҸдёҖеј з…§зүҮйғҪдјҡеёҰдёҠеүҚдёҖеј з…§зүҮзҡ„з—•иҝ№гҖӮжҲ‘зҡ„еӨ§и„‘жҲҗдәҶдёҖдёӘиў«дәӨеҸүжұЎжҹ“зҡ„жҡ—жҲҝпјҢжүҖжңүеҪұеғҸйғҪж··жөҠдёҚжё…гҖӮ
зӘ—еӨ–зҡ„зҢ«ж”ҫејғдәҶеһғеңҫжЎ¶пјҢи№ІеңЁи·ҜзҒҜдёӢиҲ”зҲӘеӯҗгҖӮе®ғжҠ¬еӨҙзңӢдәҶжҲ‘дёҖзңјпјҢзңјзқӣеңЁзҒҜе…үдёӢжіӣзқҖз»ҝе…үгҖӮйӮЈз§Қз»ҝе…үи®©жҲ‘жғіиө·еӨңи§Ҷд»Әзҡ„жҳҫзӨәеұҸвҖ”вҖ”зҢ«иғҪеңЁй»‘жҡ—дёӯзңӢи§ҒдёңиҘҝпјҢиҖҢжҲ‘еңЁй»‘жҡ—дёӯеҸӘиғҪзңӢи§ҒиҮӘе·ұзҡ„й»‘жҡ—гҖӮ
жҲ‘зңӢдәҶдёҖзңјеўҷдёҠзҡ„ж—¶й’ҹпјҡеҮҢжҷЁдёҖзӮ№еҚҒдёғеҲҶгҖӮ
иҝҷдёӘж—¶й—ҙзӮ№гҖӮеңЁеҚҒдәҢе№ҙеүҚпјҢиҝҷжҳҜжҲ‘们иҒҠеӨ©жңҖзғӯзғҲзҡ„ж—¶еҲ»гҖӮ
дҪҶзҺ°еңЁпјҢиҝҷеҸӘжҳҜдёҖдёӘдҫҝеҲ©еә—йҮҢзҡ„жҷ®йҖҡеҮҢжҷЁгҖӮзҒҜе…үжғЁзҷҪпјҢеҶ·йҘӯеӣўеҷҺдәәпјҢзӘ—еӨ–зҡ„зҢ«дёҚзҹҘйҒ“иө°еҲ°е“ӘйҮҢеҺ»дәҶгҖӮ
жҲ‘еҗғе®ҢйҘӯеӣўпјҢжҠҠеҢ…иЈ…иўӢжү”иҝӣеһғеңҫжЎ¶гҖӮ
иө°еҮәдҫҝеҲ©еә—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жҲ‘еҝҪ然жғіиө·пјҢйӮЈдёӨе№ҙйҮҢпјҢжҲ‘们зҡ„иҒ”зі»жҳҜжҖҺд№Ҳд»ҺжҜҸеӨ©еҸҳжҲҗжҜҸе‘ЁпјҢеҸҲд»ҺжҜҸе‘ЁеҸҳжҲҗиҠӮж—Ҙй—®еҖҷзҡ„гҖӮ
дёҚжҳҜж–ӯиЈӮпјҢжҳҜзЁҖйҮҠгҖӮ
еғҸжҳҫеҪұж¶Із”Ёд№…дәҶпјҢжө“еәҰи¶ҠжқҘи¶ҠдҪҺпјҢжҳҫеҮәжқҘзҡ„еҪұеғҸи¶ҠжқҘи¶ҠзҒ°пјҢеҸҚе·®и¶ҠжқҘи¶ҠдҪҺпјҢзӣҙеҲ°жңҖеҗҺеҸҳжҲҗдёҖзүҮжӯ»еҜӮзҡ„йҖҸжҳҺ гҖӮ
еғҸдёҖдёӘдәәж…ўж…ўжәәж°ҙпјҢжҜҸдёҖеҸЈе‘јеҗёйғҪжҜ”дёҠдёҖеҸЈжө…пјҢзӣҙеҲ°е®Ңе…ЁжІЎе…Ҙж°ҙйқўгҖӮ
гҖҠжҳҫеҪұгҖӢ第дә”з« пјҡж·ұеӨңзҡ„зӢ¬йЈҹиҖ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