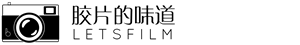зӣёжңәеҚҺдҪ—

 еҠ е…ҘеҲ°ж”¶и—ҸеҲ—иЎЁ
еҠ е…ҘеҲ°ж”¶и—ҸеҲ—иЎЁ
еӨ§жҰӮеңЁеҫҲеӨҡдәәзҡ„家йҮҢпјҢиҮід»Ҡд»ҚдҝқеӯҳзқҖеҮ жң¬еҺҡеҺҡзҡ„еҪұйӣҶпјҢйҮҢйқўзҡ„з…§зүҮеҸҜиғҪе·Із»Ҹжңүдәӣи®ёжіӣй»„пјҢз”ҡиҮідёҚд№Ҹж—©жңҹй»‘зҷҪзҡ„еҪұеғҸгҖӮйӮЈж—¶пјҢдәә们йғ‘йҮҚең°жӢҚж‘„жҜҸдёҖеј з…§зүҮпјҢ并иҷ”иҜҡең°зӯүзқҖ他们被жҙ—еҚ°еҮәжқҘеҗҺпјҢеӨ№е…ҘеҪұйӣҶйҮҢзҡ„йҖӮеҪ“дҪҚзҪ®пјҢ然еҗҺзҸҚи—ҸпјҢжҲ–дј йҳ…гҖӮ
иҖҢж•°з Ғж—¶д»Јиҝ…йҖҹж”№еҸҳдәҶеҰӮжӯӨзәӘеҝөж—¶е…үзҡ„жЁЎејҸпјҢдёҖж №ж•°жҚ®зәҝпјҢжҲ–иҖ…дёҖдёӘиҜ»еҚЎеҷЁпјҢжҲ‘们зҡ„з…§зүҮеңЁ1еҲҶй’ҹд№ӢеҶ…дҫҝеҸҜдёҠдј еҲ°зҪ‘дёҠпјҢдҫӣдј—дәәж¬ЈиөҸгҖӮиғ¶зүҮж—¶д»ЈпјҢжёҗжҲҗеӣһеҝҶгҖӮдҪҶд№ҹжңүдёҖзҫӨдәәпјҢиҝҳеңЁй»ҳй»ҳдёҺд№Ӣзӣёдјҙзӣёе®ҲпјҢжң¬ж–Үзҡ„дё»дәәе…¬йҷҲдәҡеҶӣдҫҝжҳҜе…¶дёӯдёҖдёӘгҖӮ
еңЁжІҷеқӘеққдёүеіЎе№ҝеңәпјҢйҷҲдәҡеҶӣзҡ„дҝ®зӣёжңәй“әеӯҗе·Із»ҸејҖдәҶ34е№ҙгҖӮйҷҲеёҲеӮ…д»Ӣз»ҚпјҢиҝҷ家й“әеӯҗзҡ„еүҚиә«пјҢжҳҜйҡ¶еұһдәҺеҪ“ж—¶иҘҝеҚ—ең°еҢәжңҖеӨ§зҡ„жІҷйҫҷж‘„еҪұеҷЁжқҗеҶІеҚ°е…¬еҸёпјҢеҗҢж—¶пјҢд№ҹжҳҜеҪ“ж—¶иҖҒзүҢеӣҪдә§зӣёжңәжө·йёҘгҖҒеҚҺи“Ҙзҡ„зү№зәҰз»ҙдҝ®йғЁгҖӮдәҺжҳҜжҲҗе…ЁдәҶд»–дёҺиғ¶зүҮзӣёжңәзӣёдјҙдёҖз”ҹзҡ„ж•…дәӢгҖӮ
йҷҲеёҲеӮ…жҺҘи§ҰеҲ°зӣёжңәжҜ”еҗҢйҫ„дәәж—©дәҶеҫҲеӨҡпјҢвҖңжҲ‘зҡ„жҜҚдәІеҪ“ж—¶е°ұжҳҜеңЁз…§зӣёйҰҶдҝ®з…§зүҮзҡ„пјҢжҜҸеӨ©еҺ»з…§зӣёйҰҶзҺ©иҖҚпјҢдёңж‘ёж‘ёиҘҝзңӢзңӢпјҢеҸҜд»ҘиҜҙжҳҜиҖіжҝЎзӣ®жҹ“еҗ§гҖӮвҖқдәҺжҳҜпјҢеңЁдёҖдёӘзӣёжңәиҝҳжҳҜзЁҖжңүзү©д»¶зҡ„е№ҙд»ЈпјҢйҷҲеёҲеӮ…еҜ№зӣёжңәзҡ„е–ңзҲұе·Із»Ҹжёҗжёҗжө“зғҲгҖӮ17еІҒж—¶пјҢд»–жқҘеҲ°еҶІеҚ°е…¬еҸёеҒҡеӯҰеҫ’пјҢйҡҸеҗҺпјҢиҝӣе…ҘдәҶзҺ°еңЁзҡ„иҝҷ家зӣёжңәз»ҙдҝ®йғЁгҖӮ
дҝ®зӣёжңәиҮӘ然жҳҜдёҖй—ЁжҠҖжңҜжҙ»е„ҝпјҢдёҚиҝҮпјҢз”ЁйҷҲеёҲеӮ…иҮӘе·ұзҡ„иҜқиҜҙпјҢвҖңжүӢдёҚзҙҜпјҢеҝғзҙҜгҖӮвҖқиҷҪ然з»ҸиҝҮдәҶеҮ дёӘжңҲзҡ„дё“дёҡеӯҰд№ пјҢдҪҶзӣёжңәзІҫеҜҶзҡ„еҒҡе·ҘпјҢдёҚж–ӯжӣҙж–°зҡ„еһӢеҸ·пјҢи®©дҝ®е®ҢдёҖйғЁзӣёжңәжҲҗдёәдёҖ件з ҙиҙ№еҝғеҠӣзҡ„дәӢжғ…гҖӮвҖңиҖҒејҸзӣёжңәзҡ„з»ҙдҝ®пјҢйңҖиҰҒдёҖеқ—еқ—жӢҶдёӢжқҘжЈҖжөӢпјҢе…·дҪ“жҳҜе“ӘдёҖдёӘйӣ¶д»¶еҮәдәҶй—®йўҳгҖӮеғҸдёҖеҸ°жө·йёҘзӣёжңәпјҢе°ұжңү1000еӨҡдёӘйӣ¶д»¶пјҢе…·дҪ“еҲ°дёҖдёӘе°ҸйғЁд»¶д№ҹиҮіе°‘жңүеҮ еҚҒдёӘйӣ¶д»¶пјҢиҝҷе°ұеҚҒеҲҶиҖғйӘҢиҖҗеҝғдәҶгҖӮвҖқ
жҜҸеӨ©пјҢйҷҲеёҲеӮ…йңҖиҰҒиҮіе°‘дҝ®е…ӯдёғеҸ°зӣёжңәжүҚиғҪдҝқиҜҒзӣҲеҲ©пјҢиҖҢйҒҮеҲ°иҫғжЈҳжүӢ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дҝ®еҘҪдёҖеҸ°зӣёжңәйңҖиҰҒиҖ—дёҠеҘҪеҮ еӨ©пјҢдәҺжҳҜдёӢзҸӯеҗҺпјҢеӣһеҲ°еӨ§еӯҰеҹҺзҡ„家дёӯ继з»ӯдҝ®пјҢд№ҹжҳҜеёёжңүзҡ„дәӢгҖӮжҲ–и®ёд№ҹжӯЈеӣ еҰӮжӯӨпјҢж—©е№ҙе’ҢйҷҲеёҲеӮ…дёҖеҗҢеӯҰиүәзҡ„еҗҢеӯҰе·Із»Ҹе·®дёҚеӨҡйғҪзҰ»ејҖдәҶиҝҷдёӘиЎҢеҪ“пјҢжҲ–дёӢжө·з»Ҹе•ҶеҪ“дәҶеҜҢзҝҒпјҢжҲ–иҝӣе…ҘеӯҰж ЎжҲҗдёәж•ҷжҺҲпјҢиҖҢиҝҷдёҖж–№е°Ҹе°Ҹзҡ„еӨ©ең°жҲҗдәҶд»–зҡ„еқҡе®ҲгҖӮ
еңЁйҷҲеёҲеӮ…жүҖеңЁзҡ„дёҚеҲ°еҚҒе№іж–№зұізҡ„й“әеӯҗйҮҢпјҢдёӨеј е Ҷж»ЎдәҶе·Ҙе…·е’Ңйӣ¶йғЁд»¶зҡ„жЎҢеӯҗпјҢдёүжҺ’ж‘Ҷж»ЎдәҶеҗ„ејҸзӣёжңәзҡ„иҙ§жһ¶пјҢдјҙзқҖдёҖзӣҸжӮ¬дәҺеҚҠз©әзҡ„зҷҪе…үеҗҠзҒҜпјҢдёҖжҷғе·ІиҝҮеҺ»дәҶдёүеҚҒеӨҡе№ҙгҖӮй“әеӯҗйҮҢиЈ…дёҚдёӢз©әи°ғпјҢеӨҸеӨ©д№ҹеҸӘиғҪдҫқйқ дёҖжҠҠе°ҸйЈҺжүҮе’ҢеҖҹеҠ©йҡ”еЈҒе•ҶеңәдёҚж—¶йЈҳеҮәзҡ„еҶ·ж°”еәҰж—ҘгҖӮ
д»–зҡ„дҝ®зҗҶе·Ҙе…·д№ҹеҫҲз®ҖеҚ•пјҢж”ҫеӨ§й•ңпјҢе°Ҹй’іеӯҗгҖҒй•ҠеӯҗпјҢз”ҡиҮіиҝҳжңүз”ЁеӨ№ж ёжЎғзҡ„е·Ҙе…·ж”№иЈ…зҡ„е°ҸеӨ№еӯҗпјҢз”ЁдәҺеӣәе®ҡйӣ¶д»¶гҖӮеҸҜиғҪжҳҜжәҗдәҺиҖҒдёҖиҫҲзҡ„йҖ»иҫ‘пјҢвҖңе®һз”ЁдёәдёҠвҖқпјҢжІЎжңүжүҖи°“е…Ҳиҝӣзҡ„з»ҙдҝ®жңәеҷЁпјҢдҪҶйҷҲеёҲеӮ…зҡ„жүӢиүәеҚҙжҳҜеҘҪиҜ„еҰӮжҪ®гҖӮ
вҖңеёҢжңӣиҝҷ家зҡ„иҖҒеёҲеӮ…ж°ёиҝңдёҚйҖҖдј‘пјҢж°ёиҝңжҠҠпјҲзӣёжңәпјүе°ёдҪ“иө·жӯ»еӣһз”ҹгҖӮвҖқдёҖдҪҚйЎҫе®ўеңЁйҷҲеёҲеӮ…зҡ„зҪ‘еә—дёӯеҰӮжҳҜеҶҷеҲ°гҖӮиҝҳжңүдәәжҠҠйҷҲеёҲеӮ…з§°дҪңзӣёжңәз•Ңзҡ„еҚҺдҪ—пјҢйҷҲеёҲеӮ…д»ҳд№Ӣе“Ҳе“ҲдёҖ笑пјҢдёҚд»Ҙдёәж„ҸгҖӮ
дәӢе®һдёҠпјҢеҫҲеӨҡдәәеңЁдҝ®еҘҪзӣёжңәеҗҺпјҢд№ҹеҸӘжҳҜдҪңдёәзҸҚи—ҸпјҢзңҹжӯЈеҶҚдҪҝз”Ёзҡ„е°‘д№ӢеҸҲе°‘гҖӮвҖңиғ¶зүҮзӣёжңәзЎ®е®һе…·жңүеҫҲејәзҡ„收и—Ҹд»·еҖјгҖӮвҖқйҷҲеёҲеӮ…иҜҙпјҢе’Ңж•°з ҒзӣёжңәзӣёжҜ”пјҢиғ¶зүҮзӣёжңәзҡ„дёҖдёӘзү№зӮ№жҳҜпјҢдёҚдјҡеқҸпјҢеҚідҪҝиҝҮеҺ»дёҠзҷҫе№ҙпјҢдҫқ然еҸҜд»ҘзЁҚз»Ҹдҝ®иЎҘи°ғиҜ•з»§з»ӯдҪҝз”ЁгҖӮиҝҳжңүеҫҲеӨҡжқҘдҝ®зӣёжңәзҡ„е№ҙиҪ»дәәжӣҫе‘ҠиҜүд»–пјҢе–ңж¬ўеҗ¬й’ўзүҮзў°ж’һзҡ„вҖңе—’е—’вҖқеЈ°пјҢвҖңеҫҲзҫҺеҰҷпјҢжҲ‘д№ҹе–ңж¬ўгҖӮвҖқ
йҷҲеёҲеӮ…д№ҹзҲұ收и—ҸзӣёжңәпјҢд»ҺеӣӣеҚҒе№ҙд»ЈејҖе§ӢеҲ°иҝ‘д»Јзҡ„зӣёжңәпјҢд»–иҮӘе·ұйҷҶйҷҶз»ӯз»ӯ收йӣҶеҲ°ж•°еҚҒеҸ°гҖӮиҝҷдәӣзӣёжңәзҡ„еӨ–еһӢдёҺеҰӮд»Ҡзҡ„зӣёжңәзӣёжҜ”пјҢе·Із»ҸжңүдәҶиҫғеӨ§зҡ„дёҚеҗҢпјҢи®©дәәзңӢдәҶж„ҹи§үж–°еҘҮдёҚе·ІгҖӮжҜ”еҰӮд»–жүҖ收и—Ҹзҡ„е№ҙд»ЈжңҖд№…иҝңзҡ„зӣёжңәпјҢжҳҜдёҖйғЁеҫ·еӣҪдә§зҡ„зҡ®и…”жҠҳеҸ ејҸз…§зӣёжңәпјҢз”ҹдә§ж—¶й—ҙеңЁдәҢжҲҳд№ӢеүҚпјҢиҝҷйғЁзӣёжңә收缩иө·жқҘзҡ„ж—¶еҖҷеғҸдёӘжүҒжүҒзҡ„й•ҝж–№дҪ“зӣ’еӯҗпјҢй•ңеӨҙжҳҜйҡҗи—ҸеңЁзӣёжңәйҮҢйқўзҡ„пјҢеј№еҮәжқҘеҗҺзҡ„ж ·еӯҗжңүзӮ№еғҸжүӢйЈҺзҗҙгҖӮвҖңзҡ®з®ұжңәжңҖеӨ§зҡ„еҘҪеӨ„е°ұжҳҜдҫҝдәҺжҗәеёҰгҖӮвҖқйҷҲеёҲеӮ…и§ЈйҮҠеҲ°гҖӮ
иҖҢе–ңж¬ўзҺ©ж‘„еҪұзҡ„жңӢеҸӢзҶҹзҹҘзҡ„еҸҰдёҖз§ҚеҸҢй•ңеҸҚе…үзҡ„иҖҒзӣёжңәпјҢжӢҘжңүдёҖеӨ§дёҖе°ҸдёӨдёӘй•ңеӨҙпјҢд№ҹжҳҜйҷҲеёҲеӮ…收и—Ҹзҡ„дёҖеӨ§зұ»еһӢгҖӮдёҺеҚ•й•ңеҸҚе…үзӣёжңә(еҚіеҚ•еҸҚзӣёжңә)дёҚеҗҢпјҢиҝҷз§Қзӣёжңәж“ҚдҪңз№ҒзҗҗпјҢжҗәеёҰд№ҹдёҚж–№дҫҝпјҢйҖҗжёҗиў«ж‘„еҪұзҲұеҘҪиҖ…жүҖйҒ—ејғпјҢдҪҶжҳҜиҝҷз§Қзӣёжңәзҡ„жҲҗеғҸиҙЁйҮҸеҲҷжҳҜеҚ•еҸҚжүҖдёҚиғҪжҜ”жӢҹзҡ„пјҢеңЁж”¶и—ҸиҖ…дёӯйўҮеҸ—ж¬ўиҝҺгҖӮ
йҷҲеёҲеӮ…еә—еҶ…зҡ„и—Ҹе“ҒйҮҢпјҢиҝҳжңүдёҚе°‘дёҠдё–зәӘз”ҹдә§зҡ„еӣҪдә§зӣёжңәпјҢе“ҒзүҢе‘ҪеҗҚд№ҹе…·жңүжө“еҺҡзҡ„ж—¶д»Јзү№иүІпјҢеҰӮжө·йёҘгҖҒй•ҝеҹҺгҖҒзәўжў…гҖҒеҚҺи“ҘгҖҒзҸ жұҹзӯүгҖӮеңЁйҷҲеёҲеӮ…зңӢжқҘпјҢжҜҸдёҖйғЁзӣёжңәе°ұеҰӮеҗҢеӣҪдә§зӣёжңәзҡ„зј–е№ҙеҸІпјҢвҖңеӣҪеҶ…жңҖж—©зҡ„зӣёжңәжҳҜжө·йёҘпјҢе®ғжңҖж—©еҸ«дёҠжө·зүҢпјҢеҲ°80е№ҙд»ЈпјҢд»–зҡ„еҚ•жңәдә§йҮҸжҳҜе…ЁдәҡжҙІжңҖй«ҳзҡ„гҖӮй•ҝжұҹзүҢдә§дәҺ50е№ҙд»Јжң«зҡ„йҮҚеәҶпјҢжҳҜйҮҚеәҶжң¬еңҹжңҖж—©зҡ„е“ҒзүҢпјҢжҳҜд»ҝеҪ“ж—¶зҡ„иӢҸиҒ”зӣёжңәеҲ¶йҖ вҖҰвҖҰвҖқд»–е°Ҷзӣёжңә们用塑ж–ҷзәёиўӢз»Ҷз»Ҷең°еҢ…иЈ…иө·жқҘж”ҫеңЁж©ұзӘ—йҮҢпјҢиҝҷжҳҜд»–зҡ„зҲұзү©пјҢеҗҢж—¶пјҢд№ҹи®°иҪҪзқҖд»–зҡ„йқ’жҳҘгҖӮ
йҷҲеёҲеӮ…жңүдёҖдёӘеҲҡеҲҡеӨ§еӯҰжҜ•дёҡзҡ„е„ҝеӯҗпјҢдҪҶ并дёҚж„ҝ继жүҝзҲ¶дәІзҡ„дәӢдёҡпјҢвҖңд»–жңүд»–зҡ„жғіжі•пјҢжҲ‘е°ҠйҮҚд»–пјҢеҒҡиҝҷдёҖиЎҢд№ҹзЎ®е®һдёҚе®№жҳ“гҖӮвҖқйҷҲеёҲеӮ…ж”ҫдёӢжүӢдёӯзҡ„жҙ»и®ЎпјҢеҸ№дәҶеҸЈж°”пјҢвҖңеҸӘжҳҜпјҢеҸҜиғҪзңҹзҡ„иҝҷиЎҢе°ұиҰҒеӨұдј дәҶгҖӮвҖқеңЁйҮҚеәҶпјҢз»ҙдҝ®иҖҒејҸиғ¶зүҮзӣёжңәзҡ„д»…еү©йҷҲеёҲеӮ…дёҖ家гҖӮд»–зҡ„жҺҘ件д№ҹеӨ§еӨҡжҳҜйҖҡиҝҮзҪ‘еә—д»Һе…ЁеӣҪеҗ„ең°еҝ«йҖ’иҖҢжқҘпјҢйҮҚеәҶжң¬ең°жқҘдҝ®зҡ„е·Із»ҸеҫҲе°‘еҫҲе°‘гҖӮеҸӘжңүиҝҷй—ҙе°Ҹе°Ҹзҡ„зӣёжңәй“әеӯҗпјҢиҝҳеңЁеҹҺеёӮзҡ„дёҖи§’пјҢй»ҳй»ҳеқҡе®ҲвҖҰвҖҰ
NikonFM2
50mm F1.4 AIS
Lucky SHD100